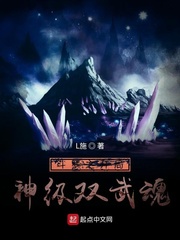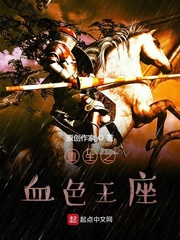酥酥的狐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这一声“我不需要”的宣告,曾在现当代不断回响着。他们走出惯常的欲望,在另一处邂逅更广阔的天地。托尔斯泰在夜间逃离生活,“只有女儿和医生陪同”,甩掉了不再需要的名誉与地位,从而到人们中去,和最穷苦的百姓生活。又有萨特拒绝诺奖,这是对当世狂热致敬的宣告,也是对“我”究竟需要什么的内在的对话。(运用比较精当的论据,拓展文意,从“我不需要”写到“我需要”。)
我想,这一句“我们需要什么”,是在清晰欲望束缚性、成就虚幻性、逃离幸福性之后,更本质的追问。苏子曾有言“物与我皆无尽也”,自然万物的无限与个人有限的对比下,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具体、实体的物的占有与欲望的满足。我们应该呼唤的,是一种生活的高度。即认识到需求的限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社会中的诱惑。冯友兰所推崇的天地境界,也正是觉解之后的回归,是欲与不欲之上的提升。(指出“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可惜冯友兰之说,用意不明,思维跳跃性过大。)
凯特·肖邦在《觉醒》中塑造了这样的形象,当埃德娜突破了“她不需要”的婚姻、社交、生活方式之后,她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世界的无限。刘瑜有言“少一点时间去沉浸于欲望的挣扎中”,“而多一点时间俯瞰生活”,在不需要之后重新理解世界,对待自我。(结尾仓促,未能很好地收束全文。)
总评:对材料的理解有深度,文章的立意有高度,可惜有些段落在思维上呈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尤其是后半部分行文仓促,章法略显凌乱。
明确欲与不欲方成人(
)
苏格拉底饮鸠自杀前,他的世交格黎东来探望他,劝他听从他的朋友携他逃监。他回复他们,不要拿什么“大众的意见”来唬人,因为大众非智慧善良之人,他们能致人死地而毫无裨益;也不要渲染外邦多么好,因为外邦人视枉法背约为稀松平常,这正是我不需要的。于是他在法律与国家的谆诰下睡去了。无怪乎他生前要感叹: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入题,以苏格拉底的认识来解析“我不需要的东西”。)
在苏格拉底这里,凡是与“公义”相左的,都是不需要的,因为市井小人的话不值得听;他只服膺真理。正如谭嗣同死前,梁启超说他终日居于日本使馆,等人来杀他,而坦言不需要名望,更不需要性命,只求以滚血换来大家的革命的热情。这是怎样的魄力!而这份坦然正来源于对“需要”和“不需要”分野的明确,对终身服膺的真理的信任,因而可以就于极刑,为真理效死而无怨言。倘若贪图之外的东西,则下地也是个不讲诚意的鬼囚,阴间的法律,如果有的话,也要与你作对。也只有明确了这条分野,人才不止于裸体猿猴,而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生命。(引入论据,阐释“需要”与“不需要”的分野所在。)
但“不需要”并不意味完全的摈弃,连听都不愿意听,没有见过黑暗的人,何能感到光明之可爱?他人的意见或者不顺耳,他人从旁聒聒或者是徒然,但不洞见时局,又何能改变时局?文学家们喜欢把故事放在茶馆、轮船等处,正是因为这里有大众的声音。扩展开去,所谓“不需要”的东西,不经过一番考察与明辨的功夫,断不能草率地斥为无用,而扔纸篓子里去了。不然人无异于一潭死水,社会将裹足不前。鲁迅讨厌许多人的论调,讨厌民众的麻木,但他从来不关上耳朵,而都写进文章里,否则头痛而医脚,没有好处。(推进文意,阐释如何对待“不需要之物”。)
这个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跳开道德、理性、补于世这层面,仍然启人深思。李贺诗文有奇才,他随身带一小囊,&#
;.
s&#
;&#
&#
;得佳句则投纸囊中,过后不复省,别人取去也绝不介怀,可谓辨于荣辱之境。他死前的诳语是人皆知道的,“帝成白玉楼”云云,仿佛只有绯衣人的声音,而自己从天上来,向天上去,世间的俗物无所需要。佛家所谓的将须弥山纳于芥子中,略无增损,也大约是这个道理:一切向内用力,向心寻求,外物与我何干?推而广之,岂止“这么多”,这整个世界都是我不需要的东西;这不是叫人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淖,而是说一切事物“内化”后才显示价值,那是“我”的东西,已不属于“物”的范围了。(由“我”的存在价值,分析如何理解“不需要”。可惜这一段说理不够顺畅,思维略显跳脱。论据与材料之间的关联不够密切。同时,未能清晰地阐明这一段与前文的关联。)
《世说新语》载:有人拜访阮籍,阮赤身在山林间,应也不应。那人离去时,大概说自己闻所闻而去,见所见而去。虽则我们不应效仿也不能效仿这仕诞的风气,但这句话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吸收我们应当吸收、愿意吸收的,其余则一毫莫取。这首先建立于广博的见闻之上,终点是内心的圆满。人最重要的也是明确需要与不需要的分野,这或者就是千年前苏格拉底的意思。(这一段论据的使用意图不明,阮籍之说未能清晰地解析题旨,反而有混淆文意之嫌。结尾照应前文,扣回材料,使结构比较完整。)
总评:对题意的理解有一定的深度,所选择的论据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对论据的分析未能很好地揭示出其与材料之间的密切关联,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