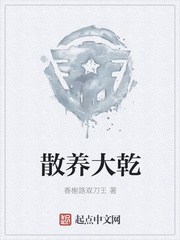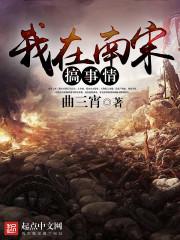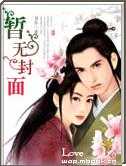泗水流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食堂吃过午饭后,赵明诚独自一人惴惴不安的来到了学官休息处。
一般生员来这里可都是受罚,但赵明诚思来想去自己除了上课摸鱼,经常请假,也没干啥有违学规的事啊,怎么就来这鬼地方了啊。
赵明诚找到标识有陈师道的斋室,木门虚掩着,想来是给他留的,于是赵明诚轻轻敲了下门扉,忐忑不安的走了进去。
进得里间,陈师道并没有午休,而是在磨墨作诗,看题款是“寄答李方叔”:
平生经世策,寄食不资身。
孰使文章著,能辞辙迹频。
帝城分不入,书札詗何人。
子未知吾懒,吾宁觉子贫。
原来是写给李廌的,感情你两都在汴京这疙瘩里,还搁这互相寄诗唱和呢,虽然你两晚年都是贫苦交加,可再多的苦诉,当面喝酒聊聊不更容易发泄出来吗,文人啊,就是闷骚!
差点忘了,赵母说过姨父陈师道是不饮酒的,其自小就体弱多病,因而长期断酒持斋诵经,企图通过诵佛经、守戒持斋等方式减轻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延长寿命。
怪不得上次撷芳楼潘意没有请到陈师道,本来按理说,陈师道位列苏门六君子,可比李格非这个苏门后四学士更为正统,名气在士人圈子里也更大,又是太学博士,自然是潘意邀请的对象,想来也是因为戒酒才没出席。
赵明诚等了好一会儿,陈师道连诗带文将其一起塞进信封,这才抬起头看向赵明诚,夸赞其在辩论时的精彩表现。
“你这诗经经义吃的很透啊,对新学、蜀学都有如此研究,最后的总结陈词更是让我大吃一惊,所获不匪。我早年间精读儒释道三家典籍,自以为勘破了门户之见。
更曾有‘大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役相与诋訾。盖世异则教异,教异则说异。尽己之道则人之道可尽,究其说则他说亦究。其相訾也固宜,三圣之道非异,其传与不传也耶’之语。
(大致意思是儒释道三教之道是一致不背的,只是因为后来世道的变化,人说的差异,从而相互诋訾,从而有了传与不传的区别。这个说法在当时算非常前卫新颖了。)
可如今看来,自己也只是那个悟不透的痴人,还需要德甫来点醒我,学问一道,孔圣人早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怎么能因门户之见,就一叶障目,不见他学之精彩呢。”
“让陈博士见笑了,微末见解,当不得此誉。”
“你这经义见解都从哪学的?整个太学就我一人会偶尔讲些蜀学内容,可我不记得给你提过苏子由的人情论。别说是从你父亲那学的,你父亲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
见陈师道当着他面贬低赵父,赵明诚自然不能当做没听到,于是据理力争道。
“姨父你那是对我爹有偏见!这次我爹出使大辽回来后,你在课堂上还以此为例,让我们修德明身,以国家大体为重,怎的这才多久,姨父就又把我爹作为没德行的人了。”
赵明诚看见自己喊他姨父时,陈师道的神色稍霁,就知道这货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内心还是很看重亲情的,于是接着打亲情牌,试图缓和赵父与陈师道的僵硬关系。虽然只见了郭姨几次,可其温婉知性的懂事模样,还是让赵明诚很心疼。
“再说东坡先生那是出于政见,才贬低于他,姨父你作为自家人,怎可也跟着人云亦云!”
这就要说到苏门与赵挺之之间的仇怨了,苏轼在元祐三年(
)十月的章疏中,说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后人因为苏轼的名声,大多是直接附和其观点认为赵挺之确实像苏轼说的那样,根本不去查看赵挺之的履历,直接将其判定为小人庸才。
就史料来看,苏、赵之争本来是推行新法和反对新法之争,但苏轼却不问事情的原由,对赵施行了人身攻击,将政见之争上升到人品之争,属实憨批。
其实际情况是赵父通判德州时,苏门的黄庭坚正监德安镇(德州之地)。赵挺之推行市易法,黄庭坚借口“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不予施行加以抵制。
然后等到“挺之召试(馆职)”时,苏轼就提出他是“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将赵父罢落,还借而说到赵父的岳父,也就是郭概是个“人材凡猥,众人共知”,可同样作为苏轼弟子的晁补之在郭概的祭文中明确说明其是一个清廉公平、守法循理之吏。
事实如何其实没啥好争辨的,当时推行的市易法,对广大较贫困的群众肯定是有利的,只不过触犯了世家豪门贵族与士大夫们的权益,被守旧派所不喜,引发政论很正常,但上升人格攻击就确实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