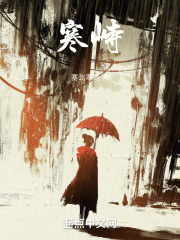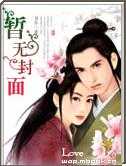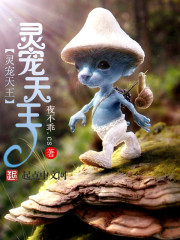作家s24fzj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棉花糖小说网www.aaeconomics.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父亲袁光福在部队服役,袁野军对他没有什么印象,虽然探亲假有一个月时间,但是来回路上差不多要五六天,在家也就二十多天时间。春节又是走亲访友的高峰期,袁光福在张淑芬的带领下,四处走亲戚,跟袁野军交流的时间很少,很难让他对父亲产生感情,他甚至还没有完全记住父亲的模样,袁光福又不得不离开家乡返回部队。不过还是有两件事在袁野军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他临走的前一天下午,总会去井里挑水,直到装满整整一水缸;一件是他回来探亲的时候,爷爷袁定国主持的团圆饭。
每年的大年初二,袁定国都会在家办招待,因为这天是几个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两个儿子又刚好在家,他自然要抓住这全家难得的团圆机会,使出他去塆上办席淘来的技术,好好在家操办一下,算是当父亲的一个责任。
初二早上,简单的吃罢早饭,李桂花就迈着小碎步来到张淑芬屋门口“张淑芬,今天少午不弄饭哦,全家都在我那里吃。”
“哎呀,大娘,又要到你那里吃饭啊,我还说今天也回娘家看看呢。”
“回娘家明天去嘛,今天那几个女儿也要回来,大家坐在一起喝点酒,还热闹些,听见没,光福。”
李桂花怕张淑芬不听劝阻,就赶忙招呼儿子,直到儿子答应下来,她又才走向大伯袁光远家。
“光远,今天少午莫弄饭哦,都到我那里吃饭,你老汉已经开始在弄席了。”
“弄啥子席嘛,都不是外人,随便炒点家常菜吃了就是,一家人还恁个客气。”
李碧华是个直爽人,有啥说啥,她知道办席是比较麻烦的事,见两个老的如此操劳,也说一些客套话。
“也不是啥子席,主要是几个门客要回来,还是得有个样子撒,要不然传出去也不好听。”
“噎,看来还是几个门客重要些哦,他们来了才办席。”李碧华听见李桂花的话,呵呵的笑起来。
“也不是办啥子席,就是那个糟老头子在操办,管他啷个弄哦,我只管打下手就是,听到没,少午莫弄饭哦!”
听见李碧华肯定的答复,李桂花又才迈着小碎步回到家中忙碌起来。老两口默契配合着:袁定国负责去井里挑水,将大石缸装满井水;取下挂在灶门前早已被熏的黑黢黢的猪头和猪脚,还有一块腊肉和几节香肠,扔在淘米水里面浸泡着;趁着泡肉的间隙,袁定国将家中的火炉搬出来,快速的将火炉点燃,不一会儿火炉膛里然起一团熊熊煤火,他赶紧将铝锅装满水放在火炉上,准备烧热水来清洗这些熏了很久的腊肉和香肠。李桂花则充当打下手的角色,做一些力所能及不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的活:将从地里摘回的白萝卜和红萝卜洗净去皮;从仓库里取出豌豆和大豆,分别用盆子泡起来,又从堆柴的地方捞了一背篼干柴放在灶门前……
这是这老两口多年生活形成的一种默契,他们并不会事先说好谁做什么,反正都是男人做重活,女人做轻活,谁忙不过来了,谁就去帮忙搭把手,几十年风风雨雨配合的默契自然。
老两口忙的不可开交,袁定国的幺女儿袁光芬端坐在屋门前忙着绣枕巾。她今年
岁,正值青春年少。农村女孩子到这个年龄阶段,都非常注重保养,都希望把自己养的白白嫩嫩,以便提高待嫁资本,找个好婆家。按照风俗,女孩子出嫁的时候,都要给亲人和亲戚准备离家礼物。这些礼物一般都是自己绣的枕巾,鞋垫,被罩等,袁光芬兄弟姊妹多,再加一些长辈亲戚,需要赠送的礼物算下来不下二十件,还要给自己准备嫁妆,全靠她一人一针一线的绣出来。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袁光芬必须提早准备。
袁光芬这些刺绣都是其他女孩子手里借过来依样画葫芦手工缝制的,一般都是“花好月圆”,“永结同心”,“比翼双飞”,“心向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出入平安”,“平安幸福”等文字。看似简单的几个字,绣起来非常讲究,她要照着样本挨个数针线走向,比如这一针是该走三线还是两线,一线之差绣出的效果会大不相同,还有针线的走向决定着字体的分布,图案就是简单的房屋或花草鸟木。袁光芬没有学过刺绣,更不懂美术排版布局,只有照着别人的样本一针一线临摹。袁光芬人年轻眼神好,对针线走向这些看的清楚的很,临摹效果一模一样,人们看了她的作品都会情不自禁的投来赞许的言语。
袁光芬并不是懒,舍不得做家务,她明白,自己嫁人后,就该承担起女主人的职责,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忙地里的活,像男人一样劳动;带孩子,给孩子把屎把尿,换洗衣服;这些都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养尊处优,那个时候再想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皮肤保养好,会与周围的人,尤其是周围的妇女们格格不入,会被人笑掉大牙。袁光芬也亲眼看见张淑芬自从嫁到袁家来,分家后如何从一个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变成一个农村女汉子的,这也是她的必经之路。如果再不抓住这美好的青春时光,人生便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和珍惜的。
对于女儿的这些变化,袁定国也是顺其自然,毕竟只剩下这一个女儿了,自己能力有限,不能给她丰厚的嫁妆,就让她自己筹备吧,到时候场面上也好看些。袁定国才五十多,正是男人顶天立地的时候,家里的农活其实也不多,最多就是忙秋收那一阵子,一般情况下袁定国是不会招呼袁光芬做家务的。他不懂什么是美,他也看不懂女儿绣的那些花花草草,儿大不由娘,她喜欢做就让她做吧,再等几年就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自己又何必把她管的死死的。
一家三口各忙各的,一切都是那样悄无声息,房顶上炊烟撩撩,不久,屋子里飘出烧肉味道,路过的人都知道这家肯定有客要来。
中午十二点,屋外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叫声,只听见袁光芬厉声呵斥“打死你这狗儿,天天喂你饭吃,你都不认识这些熟人了嗦,乱喊乱叫。”
狗通人性,看见主人在呵斥它,便摇着尾巴传出一阵呜呜声,怏怏的离去。
“三姐,你来了啊!”
远远的走来一对夫妻,男女各自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礼品,笑盈盈的朝袁定国家走来,看见袁光芬在招呼他们,脸上露出花一样的笑容,这是三女儿袁光霞一家四口。
她远嫁到龙桥乡护林村,男人名叫甘元红,结婚四年,生下两个女儿,为躲避计划生育罚款,家里的家具等值钱物件早已一无所有,甘元红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计划还要再生一胎,一定要生出个儿子才肯罢休。甘元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好在人年轻,农闲的时候跟着老乡们到大城市江州当棒棒,一个月省吃俭用下来还能往家里拿回来几十百把块钱,日子过的还凑合。
听见狗叫声,又听见袁光芬的招呼声,思女心切的李桂花也走出来迎接他们,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看见她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不由得嗔怪起来“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东西,都给我拎来了,娃儿吃啥子呢,把她们饿起啊,留给她们吃嘛。”
“那我要啷个来呢,为别打起空手来啊,遭别个笑话嗦,说我真的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连各人的亲娘都不认了哦,我这还不是往各人屋头提。”
面对亲娘的“埋怨”,袁光霞显得振振有词,她一边笑着回话一边解开背扇,将小女儿从背上放下来,袁光芬起身从背后帮姐姐接下孩子,李桂花接过三女儿的礼品,快速拎回屋里。
甘元红站在一旁笑呵呵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李桂花放好礼品后又赶紧走出来,帮着甘元红将外甥女从背上放下来。或许是背上太暖和,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十分舒适,两个孩子竟然在背上酣睡起来,两个小脸蛋红彤彤的。袁光霞解开塞在小女儿开裆裤里的尿布片,说是尿布片其实就是大人穿过的衣服裤子或者家里的床单被罩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尿布片最好是纯棉布料,不伤婴儿皮肤,农村条件有限,纯棉布料衣服很少,只好将就着用废旧衣裤改成尿布片。
袁光霞用手摸了摸尿布片,湿润的很,明显是小女儿在背上已经撒过尿,她将尿布片甩在一边,抱着小女儿开始把屎把尿,嘴里时断时续的哼着“嘘”的声音,小女儿很快尿尿了,地上留下湿漉漉的一块。过了一会儿,小女儿在她怀里不停的蹭跃,意思是她不再拉屎拉尿了,袁光霞麻利的从行李包里掏出一张尿布片塞进她的裤裆里,这才放下小女儿任由她在地上奔跑。
大女儿看见妹妹在拉屎拉尿,她也在父亲的引导下,蹲在地上开始拉屎拉尿,不一会儿,大女儿也站起来对父亲说“粑粑屙完了!”
甘元红拿出一张草纸给大女儿擦屁股。
看着两个可爱的外甥女,一到外婆家就拉屎拉尿,李桂花笑盈盈的从煤炉下铲一些煤灰覆盖在屎尿上,搅拌几下,用铲子一铲,远远的扔在坎下的菜地里当农家肥。
微微寒风吹走孩子们的睡意,姐妹俩很快恢复了活力,在空地上惊喜的奔跑着。